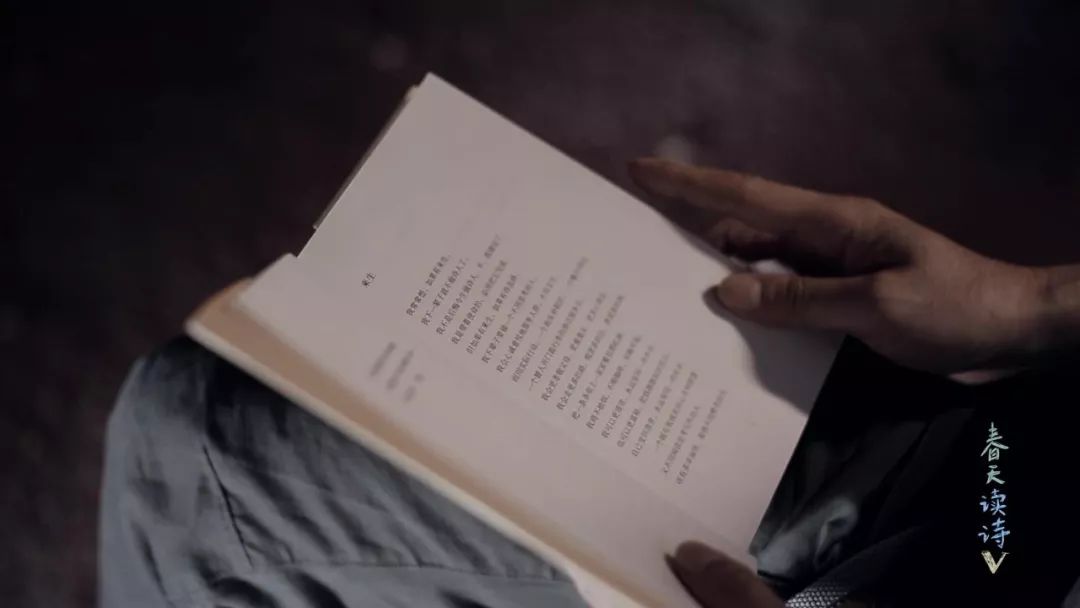我常常想,如果有来生,
我下一辈子就不做诗人了。
我不是后悔今生做诗人。不,我做定了。
我是带着使命的,必须把它完成。
但如果有来生,如果有得选择,
我下辈子要做一个不用思考的人,
我会心诚意悦地服务人群,不用文字,
而用实际行动:一个街头补鞋匠,一个餐厅侍应,
一个替人开门提行李的酒店服务员。
我会更孝敬父母,更爱妻女,更关心朋友。
我会走更多的路,爬更多的山,养更多的狗,
把一条条街上一家家餐馆都吃遍。
我将不抽烟,不喝咖啡,早睡早起。
我可以更清贫,永远穿同一件外衣;
也可以更富裕,把钱都散给穷苦人,
自己变回清贫,永远穿同一件外衣。
一个拥有我现在的心灵和智慧
又不用阅读思考写作的人
该有多幸福呀。我将不用赞美阳光
而好好享受阳光。我将不用歌颂人
而做我所歌颂的人。
——黄灿然《来生》

“可以了。”
独自坐在光影纵深处,面对镜头的黄灿然显得瘦弱而惊慌,只有手中的香烟可以暂时安抚他对这尘世的不适。翻开黄色封面的《奇迹集》,里面写着他对自己下辈子的期许:不抽烟、不喝咖啡、早睡早起……和这半辈子大相径庭的生活状态。
更重要的是——下一辈子就不做诗人了。

很多时候,当我们用假设的口吻谈来生,其实只是在观照当下的心境,还有那些扑空与错过的今生的愿望。
人生只有一次,没办法把所有的人生样态都过活一遍。从笃定地选择做一个诗人并以此为命运的那一刻起,这一世的黄灿然就注定了终生都得去思考、去和自己纠缠、去追问世事。
他其实是安于诗人这个身份的。他生来就有诗人的特质,从田野里、村子里、半空中汲取养分;他着实对身外的大千世界都充满感觉,他可以对着电线上的鸟儿吹口哨,也可以长久地注视着石板巷里一窝刚出生的小猫,任何寻常的街景、日落、行人,甚至路边的一块小石子,都能在其心中荡起涟漪。他太敏感了,迫不及待想要去抓住所有映入眼帘、所有打动自己的事物,并用精准的词汇去捕获它们、记取它们。

他没办法不做诗人,因为太爱这个世界和世间的一切。翻看黄灿然的诗集,你会发现,生活的细微日常全都可以成为他写诗的由头,那些被你漠视的、不以为然的匆匆过客,全被他的诗持久定格和永恒延展:城市的人行道上看到的妇女、上班巴士上遇见的青年、美丽的女孩、内向的老人…….他执迷于他们的神色,并试图去揣测他们面孔背后的静水深流,即使这些人只和他打了个照面。
只是作为诗人的人生,也有其不堪承受的重。所有描述、思考、追问,也许都只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过程,那个过程折磨你、撕扯你,让你陷入某种虚空,陷入无意义。很多年前,郁达夫就曾这样检视过自己:”若说人的生活可以涂抹了改作的时候,我的第二次的生涯,决不愿意把它弄得同过去的二十年间的生活一样的!我从小若学做木匠,到今日至少也已有一二间房屋造成了。无聊的时候,跑到这所我所手造的房屋边上去看看,我的寂寥,一定能够减轻。我从小若学做裁缝,不消说现在定能把轻罗绣缎剪开来缝成好好的衫子了。无聊的时候,把我自家剪裁,自家缝纫的纤丽的衫裙,打开来一看,我的郁闷,也定能消杀下去…… ”这可能是大多数文人的通病:以为自己若是从事别的看起来更实实在在的工作,也许会活得轻松容易些。这不过是思考了太久的人的精神缓解剂罢了。

但黄灿然是真的热爱这世间的一切人和一切职业。他的诗里,写过一个叫肥仔的杂务员,健康、勤劳、幽默,服侍自己也像服务别人那般近于神圣;他也写过熨衣服的老人,在整洁的店面里安静地工作,给凌晨下班回家的人以灵魂的慰藉。这些用实际行动服务别人的工作,不需要思考,却可以用生命的热忱原力去拥抱生活,也许反而更接近生活的本质。所以黄灿然才会在另一首诗中说:”对于想从事诗歌艺术的人,我鼓励/生活美好,但诗歌艺术更美好。/对于想退出诗歌艺术的人,我鼓励:/诗歌艺术美好,但生活更美好“
诗人一样要生活。为了完成诗人的使命,黄灿然做着繁重的翻译工作,靠微薄的稿费维持基本生活,偶尔遭遇变故便只能求助于朋友的接济。他用自己今生的清贫喂养着永世的诗歌。可如果有来生,他却愿意更清贫,只要能好好享受阳光。当然“也可以更富裕,钱都散给穷苦人“,做一把自己歌颂的人,哪怕变回清贫,哪怕”永远穿同一件外衣“。

来生可以做的还有很多。比如“更孝敬父母,更爱妻女,更关心朋友“,把那些今生做得不够好的事情做得更好;比如”走更多的路,爬更多的山,养更多的狗,把一条条街上一家家餐馆都吃遍“,体会所有最简单的幸福……
可是,真的有来生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