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擅长写作的人?听到这个问题,也许您会哑然失笑:这还用问,非作家莫属。对于作家,世人大多存有浪漫的幻想,认定在他们的脑袋瓜里头,含有某种可以被称为写作思想的神秘物质。而作家的双手,掌握着某种常人所不具备的写作技巧。两者结合,文字就会自然而然地流淌于纸张,形成一篇又一篇精美的文学作品。
如此说来,作家亲口陈述的写作经验,不仅是第一手的宝贵资料,更是如假包换的“武功秘籍”。这是否意味着,只要文学爱好者能够韦编三绝,参透其中奥秘,也有机会跻身伟大作家的行列?且慢,关键问题在于,作家谈写作,就一定靠谱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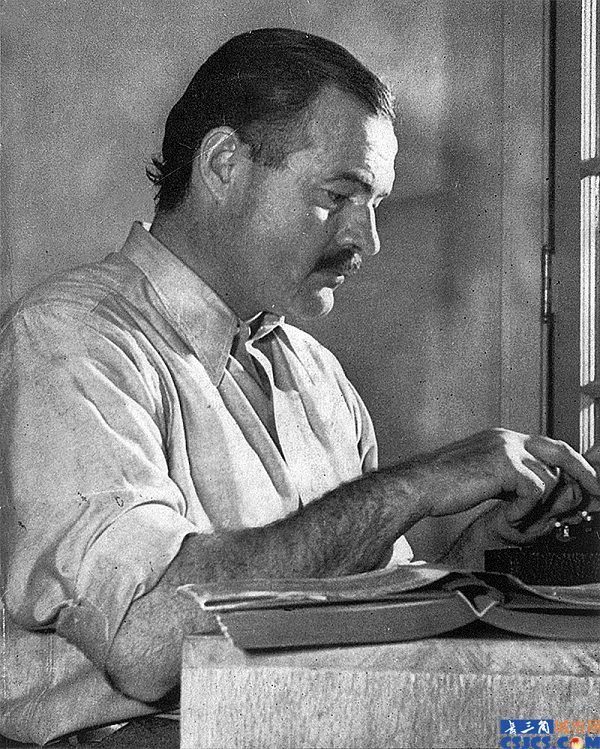
在写作的海明威
论写作,首先得明确,为什么写?前辈作家曹丕,早就将写作的地位抬高到“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。在《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》中,梁启超不无夸张地表示:欲新一国之民,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可见,在传统文学观中,写作是一件为时代、为国家、为民族的大事。
不过,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认同这一观点。新小说代表人物阿兰·罗伯·格里耶就认为,当小说家“有话想说”时,这其实是一个讯息。其中有政治的内涵,或是宗教的讯息,或是宗教的法令。对萨特来说,这是一种“干预”。但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。格里耶推崇的是福楼拜,因为他“描写了一个完整的世界,但他却没有任何话要说,换句话说,他没有任何讯息想传达,对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拿不出一剂良方。”
格里耶的观点就和他的小说一样耐人寻味。事实上,如果不了解新小说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反动,普通读者就很难领会他的想法。格里耶早就说过,“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,也不是荒谬的,它存在着,如此而已”。所以,对于传统小说念兹在兹的主题思想,新小说自然是不屑一顾的。可是,要是某位不明就里的同学,误认为把早餐吃了啥描写一番就是一部传世之作,难免贻笑大方。

《给青年小说家的信》
或许,爱丽丝·门罗的看法更接地气一些。在接受《巴黎评论》的采访时,她坦承,不写作就会让她无所适从。她说道,“有可能停止写作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惊慌——就好像我一旦停下来,我可能会永远停止写作。我脑子里可是储存了一堆的故事。”可见,门罗并不认为写作带有功利性,而应是一项能够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活动。不过,若有人因此将写作理解为纯粹的自娱自乐,这就是天大的误会了。读过门罗作品的读者都能体会到,她对女性生活困境的描述是何等深刻。看来,写作的目的本就因人而异,粗线条的划分并不可取。何况,这也保证了作品的多样性和多元化,不是吗?
明白了为什么写,还得解决写什么、怎么写的问题。关于这一点,略萨在《给青年小说家的信》中谈道,“小说家不选择主题,是他被主题选择。他之所以写某些事情,是因为某些事情总在跟踪、纠缠、骚扰他。他不得不写。像一个魔鬼,主题折磨他。”不愧为大作家,略萨的描述可谓形象至极。可是别忘了,纵观略萨的一生,他都在和拉丁美洲以及秘鲁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。对于自由的强烈渴望,引发了他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。正因如此,才会有不可胜数的主题找上略萨的门来。如果某位同学自认为坐在家中,刷刷微博微信,就会受到主题的“折磨”,那可就麻烦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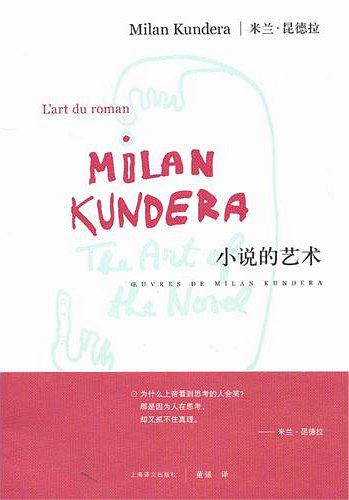
《小说的艺术》
米兰·昆德拉谈得更具体些。在《小说的艺术》中,他指出,“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,一种探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、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。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。”这是何其精妙的解释,难怪昆德拉先生能为文学青年提供数之不尽的人生金句。回想一些伟大作品的名称吧:《红与黑》《理智与情感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战争与和平》……只是,找到特别的词,并不能保证您就能写出一部优秀的小说。要知道,托尔斯泰描写“战争”与“和平”,是为了突出人民的崇高与伟大,深刻揭示出推动历史前进、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这一历史规律。这可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水平。
决定写什么之后,就得考虑怎么写。许多伟大作家都拥有独门绝技,同时也愿意大方地与读者分享。比如海明威著名的“冰山原则”。他谈道,“《老人与海》本来有一千页以上,把村子里每个人都写进去,包括他们怎么谋生、出生、受教育、生孩子等等。有的作家这么写,写得很好很不错。写作这行当,你受制于已经完美的杰作。所以我得努力学着另辟蹊径。”冷静、克制成就了《老人与海》,可这是说易行难。瞧瞧动辄上千万字,不成鸿篇巨制决不罢休的无数网络文学吧,您就能明白,想要做到惜墨如金,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对于小说的结构和语言,卡尔维诺有话要说。在《美国讲稿》中,他讲解了小说的“轻与重”。 卡尔维诺认为,他的工作是“有时减轻人物的分量,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,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,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。”乍听之下,卡尔维诺的技法有些玄乎。其实,阅读过《堂吉诃德》的朋友,不难理解他的意思。如何用看似轻松的笔调,描写沉重的人生悲剧,塞万提斯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。当然,理解是一回事,能不能做到,还得看个人的悟性和天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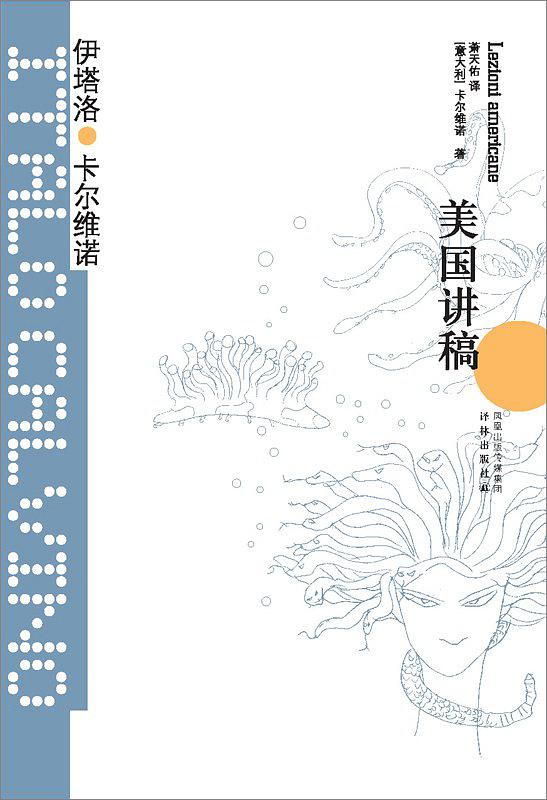
《美国讲稿》
那么,普通人有没有办法通过勤学苦练,提升写作功力?至少在杜鲁门·卡波特看来,这并不难。《巴黎评论》向他提问:是否存在提高写作技巧的利器?卡波特如是回答:“据我所知,多写是唯一的利器。写作具有关于透视、影调的一般法则,就像绘画或者音乐一样。如果你生而知之,那很好。如果不是,那就要学习这些知识。然后将他们以合适你的法则重新编排。即便是我们那位最傲慢的乔伊斯,也是个超级工匠,他之所以能写《尤利西斯》,是因为他能写《都柏林人》。”多学、多写,卡波特给出的建议不掺一点水分,实在得很。虽然如此,我们也该清醒地认识到,并不是人人都能写出《都柏林人》的。
看来,作家谈写作,纵然是肺腑之言,也不宜被追捧为唯一的金科玉律。毕竟,写作本就是一件极度个人化的工作。亦步亦趋、缺乏原创性的作品,没有生命力可言。伟大作家的写作方式,绝非万能钥匙。劳伦斯·布洛克在《布洛克的小说学堂》里端出了一碗毒鸡汤:“老天,绝大多数小说都卖不出去,它们凭什么一定要卖得出去?我从没听说过哪行哪业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。”虽然不中听,但恐怕这才是无数人写作生涯的真实写照吧。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