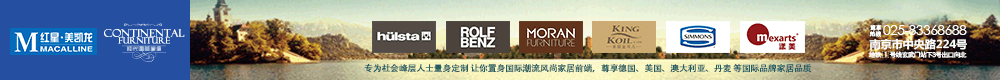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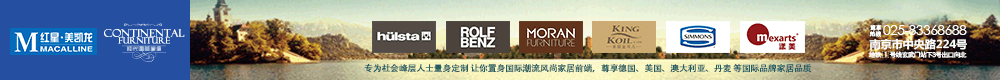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梁武帝普通三年刻立于茅山南洞口的《九锡真人三茅君碑》,为理解以句容茅山为中心的南朝信仰地理提供了珍贵线索。题名于碑的“齐梁诸馆高道”人数众多,籍贯明确,呈现出侨旧混杂的特征。从身份上说,三茅君是三位原籍关中、渡江成为茅山之主的“神仙侨民”。这种侨寓情节的三茅君传记,出现于杨、许降神的东晋中期。三茅君被赋予的信仰职责是“监泰山之众真,总括吴越之万神”,即主管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,具有融合侨旧的信仰面貌。在这种“宗教想象力”的影响下,茅山成为道教圣地,刘宋以后道馆日渐增多,齐梁时期臻于极盛。这些道馆多由皇室敕建或大族供养,馆务“劬劳”,并非纯粹支持个人修道。在梁武帝中期佛教日益兴盛的形势下,道教徒在圣地茅山建造总结三茅君信仰的纪念石刻,具有一定的宗教抗争意味。
【关 键 词】茅山/三茅君/神仙/侨旧/南朝
【作者简介】魏斌,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。
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及其带来的区域历史变动,是东晋南朝史研究最核心的课题之一。近一个世纪以来,国内外学界在侨吴士族关系、侨州郡县及流民分布、黄白籍、土断等问题上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成果。①不过,由于史料不足征等原因,侨民在江南新居地的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图景,仍然很不明晰。②比如说,在江南侨民最为集中的京口、晋陵和建康以东沿江地区,③侨民所带来的生计习惯和文化观念,如何在新居地植根存续?是否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的江南旧民?江南旧民又如何面对侨民及其文化?如果没有更为细致的区域性史料,这些问题很难落实到具体地理空间内进行观察。
句容茅山的道教史料群由此显得弥足珍贵。《真诰》、《周氏冥通记》中记录了大量有关茅山道教活动的细节,其价值早已广为人知。而一类更直观的史料——碑石及其铭文,由于原石多已亡失,尚未受到足够重视。这些当时分布于山中各处的纪念性石刻,蕴含着理解句容茅山区域史的丰富线索。其中,梁武帝普通三年(522)由建康崇虚馆主、道士正张绎主持刻立于茅山南洞口的《九锡真人三茅君碑》,由于其信仰总结意味和大量有明确身份、籍贯的题名,学术价值尤为重要。本文计划从此碑入手,结合相关石刻及《真诰》、《周氏冥通记》等文献记载,从社会史层面探讨句容茅山的兴起及其意义。
句容茅山以上清派的修道圣地而著名。④茅山中的句曲山洞位列道教十大洞天之八,⑤在《真诰》的“神启”中,“吴句曲之金陵”与“越桐柏之金庭”并称,被认为是“养真之福境,成神之灵墟”,“吴越之境唯此两金最为福地”。⑥不过,葛洪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曾历数当时可以修道合仙药的江南名山,句容茅山并不在其列。⑦葛洪就是句容人,他对茅山的“忽视”,说明直至东晋初期茅山仍非修道圣地。根据《真诰》及相关文献来看,茅山被赋予特殊宗教意味,其实就肇始于东晋中期杨羲和许谧父子的降神活动,而真正成为道馆集中的修道圣地,则要到刘宋以后特别是齐梁时期。
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句容茅山的圣地化?稍读《真诰》等文献就会发现,神仙三茅君兄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许谧父子的修道之路由其指引,南朝时期茅山每年最隆重的信仰集会也与其有关。值得注意的是,三茅君本是成阳南关人,后渡江成为茅山之主,主管着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。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。神仙三茅君的侨民身份是否与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有关?三茅君信仰的兴盛和茅山的圣地化,是否反映出江南侨民、旧民的融合关系?⑧这正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。
一、普通三年茅山立碑事件
《九锡真人三茅君碑》原石今已不存,录文收入元代茅山道士刘大彬所编的《茅山志》。原碑内容由五部分构成:(1)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锡玉策文;(2)三茅君小传;(3)碑铭(叙述茅君事迹、立碑缘起等);(4)碑阴题记(记述立碑时的神异现象);(5)题名(“齐梁诸馆高道姓名”;唐宋时期续有补题,阙失未录),分别收入《茅山志》卷1《诰副墨》((1))、卷20《录金石》((1)(2)(3))、卷15《采真游》((5))。⑨其中,(1)(2)(3)记述三茅君的策命文字和生平事迹,内容与《茅山志》卷5《茅君真胄》、《云笈七签》卷104李遵《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》大体相似而更简略。⑩由于《茅君真胄》和李遵传记的存在,(1)(2)(3)的相关内容除了具有校勘方面的价值外,史料意义不大。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除了少数研究者简略提及(5)的题名价值外,(11)此碑较少受到关注。
其实,古代碑石的史料意义,并不仅仅是刻写于其上的文字。碑石刻立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仪式过程。如果把普通三年三茅君碑的刻立,还原为一次集体性宗教事件,就会发现其中提示出很多有趣的历史线索。具体来说,为何刻立此碑?哪些人参与了这次活动?立碑时间、地点的选择是否有特殊考虑?沿着这些线索分析,再结合碑阴题名内容,普通三年茅山的信仰图景和此碑的史料价值,就会逐渐显现出来。
这次立碑有其特定的信仰背景。齐梁时期,茅山的信仰活动颇为兴盛。这种兴盛一方面体现在山中道馆林立,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每年三月十八日道俗云集的登山盛会。《真诰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“三月十八日”条陶弘景注云:
唯三月十八日,公私云集,车有数百乘,人将四五千,道俗男女状如都市之众。看人唯共登山,作灵宝唱赞,事讫便散,岂复有深诚密契、愿睹神真者乎?纵时有至诚一两人,复患此喧秽,终不能得专心自达。三月十八日是大茅君来游茅山之日,《茅君真胄》云:“三月十八日、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师及南岳太虚赤真人游盻于二弟之处也,将可记识之。有好道者待我于是日,吾自当料理之,有以相教训于未悟。”(12)这种明确的指示,自然引起修道者瞩目:“好道者欲求神仙,宜预斋戒,待此日登山请乞。笃志心诚者,三君自即见之,抽引令前,授以要道,以人洞门,辟兵水之灾,见太平圣君。”(13)大茅君来游每年有两日,但据《真诰》可知,十二月二日由于天气寒冷,“多寒雪”,来的人很少。而三月十八日正值“江南草长,杂花生树,群莺乱飞”时节,登山乞神,场面相当壮观。
从陶弘景的描述可知,三月十八日登山乞神的“四五千人”之中,不仅仅是道士,也包括很多世俗信徒。他们主要的活动是登山,“作灵宝唱赞”,具有很强的仪式性。尽管陶弘景对这种集会颇多批评,但其中揭示的三茅君信仰的活力,(14)却让人极感兴趣。普通三年刻立的三茅君碑,当然也是在这种信仰背景下出现的。
立碑事件的主持者是“三洞弟子领道士正”吴郡张绎。道士正是梁武帝天监二年(503)设立的道官,有大、小之分。平昌人孟景翼天监初年曾担任大道士正。(15)从三茅君碑题名还可获知,张绎是以建康崇虚馆主身份兼道士正,统领道教事务。(16)这意味着三茅君碑的刻立带有一定官方色彩。碑文说:
有道士张绎,欣圣迹之预闻,慨真颜之不睹,念至德之日道,惧传芳之消歇,故敬携同志,谨镌传录,虽复罗衣之屡拂,冀巨石之不糜,面千龄而沥肾,对万古以披心。但恨言不足以尽意,庶冥鉴之匪尤。由这通张绎本人撰写的碑文可知,(17)立碑刻写三茅君“传录”,是希望三茅君事迹能够传之久远,“长怀万古”、“传石留声”。他所提到的“同志”,当指“略见”于碑阴和碑侧的90余位“齐梁诸馆高道”。(18)这份名单为了解齐梁时代的茅山道教世界,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资料。略感遗憾的是,《茅山志》将其著录于《采真游》,而非直接附于碑铭之后,给利用这份题名带来一些麻烦。
题名至“治丞法身山阴董道盖”为止可以确认。问题在于自谁开始。主持其事的是道士正张绎,照理说他应当列于题名首位,但题写形式有些不符。题名一般包括馆名、籍贯、姓名三项(如“洞清馆主兰陵车龄晚”),《采真游》“张绎”条则是:“崇虚馆主道士正吴郡张绎。馆本宋明帝敕立于潮沟,供养大法师陆修静。齐永明敕立于蒋陵里。陶先生再兴焉。”开始符合一般形式,其后多出有关崇虚馆兴替的记述。紧随张绎之后的徐公休、张玄真、张景遡诸条,也有“善有道素”、“道兼三洞”、“秀挺超群”等文字。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?《宝刻丛编》卷15“梁茅君碑并两侧题名”条引《复斋碑录》提示了一些线索:
碑阴右侧题三洞法师真人殷灵养;左侧题三洞法师鲁郡周显明,以己卯诞世,寻真宋末,德茂齐梁。(19)
殷灵养、周显明均见于《采真游》,题写形式为:三洞法师曲阿殷灵养、三洞法师鲁郡周显明。比较两种著录可知,周显明题名之后本来还有“以己卯诞世,寻真宋末,德茂齐梁”等文字。(20)此外,《采真游》“孙文韬”条亦称:“南洞碑阴云:文韬心柔容毅,迹方智圆。既业不群物,故异简刊焉。”可见孙文韬题名之后也有相关文字。由此可以获知,题名于碑阴和碑侧的90余位“齐梁诸馆高道”,不少应当都附有介绍、评价性文字。这些文字在《茅山志》编纂时大部分被省略了。从顺序上来看,《采真游》中孙文韬在张绎之前。据此并结合传记内容推测,《采真游》中自“上清道士丹阳葛景宣仙公之胤”到“嗣真馆主丹阳句容许灵真”诸人,很可能也是题名内容。(21)
如果仅从张绎开始算起的话,题名共计91人。从身份来说,有以下几种:(1)天师后裔:包括天师九世、十世孙和孙女,共有10人;(2)馆主、馆主女官、精舍女官:这是题名的主体,共有68人;(3)道士、女官:4人;(4)三洞法师:3人;(5)逻主:1人;(6)法身:5人。题名者所属的道馆,有不少可以确定位于茅山。如华阳馆、崇元馆、曲林馆、金陵馆、北洞馆、天市馆、方隅馆、金陵馆、招真馆等;有的则不在茅山,如林屋馆当位于太湖中的林屋山洞。(22)但绝大多数道馆位置缺考。(23)
题名者的籍贯分布最令人感兴趣。上述91人为主,加《采真游》张绎之前、葛景宣之后数人(包括有明确记载的孙文韬)。分郡县统计可知,晋陵郡人数最多,有34人;其次是丹阳郡19人,吴郡11人,南琅琊郡8人;然后是会稽郡4人(1人为僧人),义兴郡4人,吴兴郡2人,南东海郡2人;另外有侨民8人,天师后裔10人,不详籍贯者2人。可见题名于碑者主要来自于茅山周边地区,特别是邻近的晋陵郡和丹阳郡等地,同时也波及太湖周边的吴郡、义兴和更远的会稽。从身份上来说,则兼有侨民和旧民。
陶弘景弟子参与了这次立碑活动,碑文书法即出自弘景弟子孙文韬之手。但现存题名中没有出现陶弘景的名字,也许是《茅山志》编纂时的省略。张绎和陶弘景曾就《法检论》有过“往复讨论”,(24)两人是相识的。张绎主持在茅山建立三茅君碑,陶弘景应当会参与其事。但从立碑地点分析,又有些蹊跷。此碑立于茅山华阳南洞,也被称作南洞碑。《茅山志》卷7《括神枢·坛石桥亭》:“九锡亭,在南洞,以覆九锡文碑,石柱篆刻。”同书卷6《括神枢·洞》:“黑虎洞,在华阳南洞九锡碑之左。”又云:“黄龙洞,在九锡碑之右。”可知碑呈石柱状,篆刻,位于华阳南洞,居黄龙、黑虎两洞之间,元代时有亭覆盖其上。华阳南洞位于大茅山南麓,距陶弘景居住过的积金岭、雷平山、郁冈都比较远。(25)
关于茅山的地理概况,陶弘景有过概括介绍。茅山是一组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峰的总称,山势曲折,“状如左书巳字之形”:
今以在南最高者为大茅山。中央有三峰,连岑鼎立,以近后最高者为中茅山。近北一岑孤峰,上有聚石者为小茅山。大茅、中茅间名长阿,东出通延陵、[句]曲阿,西出通句容、湖[就]孰,以为连石、积金山,马岭相带,状如埭形。其中茅、小茅间名小阿,东西出亦如此,有一小马岭相连。自小茅山后去,便有雷平、燕口、方嵎、大横、良常诸山,靡迤相属,垂至破罡渎。自大茅南复有韭山、竹吴山、方山,从此叠障,达于吴兴诸山。(26)据《真诰》记载,茅山句曲山洞有五个便门,分别是南两便门、东西两便门和北大便门。便门是句曲洞天与外界交通的门户,为修道者所重视。但其中只有山南大洞、北良常洞比较显露,另外三处很难寻觅,陶弘景指出:“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门,东门似在枝陇中,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门,而东西并不显。”(27)正由于此,山南大洞附近较早成为道馆集中之地。(28)不过,这里的信仰状况颇为芜杂:“自二十许年,远近男女互来依约,周流数里,廨舍十余坊。而学上道者甚寡,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而已。近有一女人来洞口住,勤于洒扫,自称洞吏,颇作巫师占卜,多杂浮假。”这样来看,山南大洞附近主要是“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”的道士以及巫祝的活动场所。陶弘景对此很不满意,批评说:“今南便门外虽大开而内已被塞,当缘秽炁多故也。”这个评论耐人寻味。意在使神仙三茅君“长怀万古”的《九锡真人三茅君碑》,为何会选择在被陶弘景批评为“秽炁”的山南大洞口呢?
不仅如此。南洞碑建立的普通三年五月,远在小茅山以北的雷平山麓,竟然也有碑刻活动,这就是《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》。(29)碑文为陶弘景所撰,内有“十七年,乃缮勒碑坛,仰述真轨”之说,据此天监十七年此碑已刻写建造。但碑阴题名之后又记:“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。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略记。”时间记述上出现了差异。这种差异是由于补刻而造成的。从内容上看,许长史碑阴分为两部分:陶弘景小传、题名(上清弟子、皇帝朝臣等)。其中,陶弘景小传记述其主要活动,至天监十五年“移郁冈斋室静斋”为止,据此推断,小传应当也是天监十七年刻写上石的。而仔细体味碑阴末尾的“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”云云,可知普通三年补刻的只是皇帝、朝臣题名。题名中谢举的官号“侍中、豫章内史、太尉长史”,综合了其天监十四年至普通元年间的主要任职,也可佐证此点。(30)至于上清弟子题名,应当是天监十七年和碑文、小传一起刻写上石的。(31)
普通三年的这次补刻引人注目。天监十七年的刻石,与陶弘景自立冥所的时间相近,可能是陶弘景根据真人指示筹备身后事宜的举措之一。(32)后者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许长史碑补刻于五月五日,南洞碑建立于五月十五日,前后仅相隔十天。这是否只是一种巧合?如果不是,这次补刻与三茅君碑的建立又有何关联?
普通三年茅山南洞口的立碑事件由此显得颇为特别。这次由建康道士正主持、牵涉到近百位道士和供养人、颇有神异色彩的集体性立碑活动,(33)至少提示出以下几个问题:(1)与均为上清弟子题名的许长史碑相比,三茅君碑题名包括天师后裔、三洞法师、上清道士等多种身份,他们为何成为“同志”,共同参与三茅君碑的刻立?(2)从题名者地域分布来看,江南流民集中的晋陵郡、丹阳郡等地,江南土著势力强大的吴郡、义兴郡等地,都有不少人参与。三茅君究竟是怎样的神仙,会受到侨民、旧民的共同崇奉?(3)立碑地点为何选择在陶弘景极力批评的华阳南洞口?时间为何是在普通三年?为何十天前会有许长史碑的补刻?很明显,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是三茅君的信仰内涵。
二、“神仙侨民”与江南新乡土
据三茅君碑、《茅君真胄》和《云笈七签》本李遵《司命真君传》,大茅君名盈,成阳南关人,曾在恒山学道,后受学于西城王君,汉元帝(一说汉宣帝)时升仙,渡江居于句曲之山,“邦人因改句曲为茅君之山”。后来他的两个弟弟茅固、茅衷亦于汉元帝永光年间渡江至茅山。至汉哀帝元寿二年(前1年),大茅君受太帝命为司命东卿上君,治赤城玉洞之府,离开茅山。茅固(中茅君)、茅衷(小茅君)为地仙,分别为定录真君和保命仙君,留居茅山。大茅君离开时约定,每年三月十八日、十二月二日来访。
有关三茅君传记的相关文本,道教史学者已有过不少讨论。综合相关意见来看,基本可以确认,记有上述内容的三茅君传记出现于东晋中期。⑤最重要的证据,是《真诰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所记许谧答信:
昔年十余岁时,述虚闲耆宿有见语,茅山上故昔有仙人,乃有市处,早已徙去。后见包公问动静,此君见答,今故在此山,非为徙去。此山,洞庭之西门,通太湖苞山中,所以仙人在中住也。唯说中仙君一人字,不言有兄弟三人,不分别长少,不道司命君尊远,别治东宫。未见传记,乃知高卑有差降,班次有等级耳,辄敬承诲命,于此而改。校注指出,“未”当作“末”。许谧生于永兴二年(305),“十余岁”时正是两晋交替之际,其时故老口传只是说“故昔有仙人”,并无三茅君传说。后从包公(鲍靓)处听说仙人是茅季伟。这个说法在《晋书》卷80《许迈传》中可以得到印证:“谓余杭悬霤山近延陵之茅山,是洞庭西门,潜通五岳,陈安世、茅季伟常所游处。”(35)在三茅君传记中,中茅君名固,字季伟,但许谧读到传记之前,显然并不知道茅季伟就是中茅君。他大概有些奇怪,为何鲍靓只告诉他中茅君的“字”。其实事情已经很明确,杨、许降神之前与茅山有关的茅姓仙人,就只有一位茅季伟。(36)而且据鲍靓和许迈所言,其时茅山在神仙世界中的地位是依存于洞庭山的(洞庭之西门),远非后来可比。
许谧得读三茅君传记,是在“乙丑年初”,即兴宁三年(365)初。传记应当是随着杨、许降神活动一起问世的。传记是真人之诰的辅助文本,目的是吸引许谧皈依“上道”。(37)那么,在这种背景下“出场”的神仙三茅君兄弟,具有怎样的特征呢?
三茅君传记并不完全是新建构的,其基础是早期《神仙传》中的茅君传记。(38)不过,这位茅君是幽州人,学道于齐,(39)新传记将其籍贯改为咸阳南关,是很大的不同。这种改变的原因已很难确知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真诰》卷17《握真辅第一》录有数条关中地区的地理、遗迹和传说,其后陶弘景有一条有趣的按语:
右此前十条,并杨君所写录潘安仁《关中记》语也。用白笺纸,行书,极好。当是聊抄其中事。陶弘景对于杨羲为何抄写《关中记》,显然并不太清楚,故而判断为“聊抄”。其实,结合三茅君新籍贯来看,可能并非如此。《真诰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记定录君之语,称茅山金陵之土坚实,“掘其间作井,正似长安凤门外井水味”。又说:“子其秘之。吾有传纪,具载其事,行当相示。”这条诰示的时间显然在许谧得读三茅君传之前。其中“正似长安风门外井水味”一句,流露出原籍咸阳的中茅君对“故土”的熟悉。由此判断,杨羲抄读《关中记》,应当是为了获得有关关中地理的知识。
在李遵撰本茅君传记中,茅君自咸阳渡江至茅山,成为神仙世界的“侨民”。这个情节在早期《神仙传》中也不存在,而是记其成仙后:“去家十余里,忽然不见,远近为之立庙奉事之。茅君在帐中,与人言语,其出入,或发人马,或化为白鹤。”(40)这位茅君显然是在故乡成仙,又佑护着乡里之人。为何李遵撰本中茅君会长途跋涉来到茅山,成为“神仙侨民”呢?细读《真诰》就会发现,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。《真诰》中登场的神仙,绝大多数都来自吴越以外的地区,如卷1《运象篇》列有一份南岳夫人诰示的神仙名单,籍贯包括咸阳、郑、卫、幽、沛、常山、长乐、楚、东海、冯翊、涿郡、西域等地。(41)出场最多的几位神仙,如紫阳真人周君是汝阴人,(42)清灵真人裴君是右扶风人,(43)杨羲仙师南岳夫人魏华存是任城人,均来自北方。其中,魏华存嫁于南阳刘氏,丈夫去世后,“为真仙默示其兆,知中原将乱,携二子渡江……自洛邑达江南”。(44)许迈曾师从的鲍靓(其女嫁与葛洪)是东海或陈留人,于东晋大兴元年(318)南渡。(45)河中人平仲节则在“大胡乱中国时”,渡江入括苍山。(46)可见在《真诰》中,“神仙侨民”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身份特征。(47)
关于“神仙侨民”迁居江南的具体情形,《神仙传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。东海郡人王远(字方平),为乡里陈耽所供养,后来“蛇蜕”而去,南渡入括苍山,途经吴郡之时,住在“骨相当仙”的胥门小民蔡经家,点化其成仙。后来又再次降临蔡家,招来东海女神麻姑,显示种种仙术。根据蔡经的描述,王远“往来罗浮、括苍等山”,“主天曹事,一日之中,与天上相反覆者十数过。地上五岳生死之事,皆先来告王君。……所到则山海之神皆来奉迎拜谒”。(48)王远在故乡东海郡仙去后,渡江至江南,仙职与“地上五岳生死之事”有关,这些情节与“总括东岳”、“领死记生”的三茅君颇为相似。王远在吴郡与蔡经的接触,与三茅君对许谧的引导和教化,也有可比之处。
这种“神仙南渡”叙事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方流民的南迁。分析起来,“神仙南渡”的原因,可能主要有两个:其一是流民将所崇奉的神仙带到了江南新居地;其二是神仙知识的传承者和制造者——道士们——的南渡。前一种情况相关记载较少,暂且不论;后一种情况在《抱朴子内篇》、《真诰》等文献中均有不少记载。根据这些记载来看,道士群体的南渡,集中在东汉末年和永嘉之乱两个时期。
东汉末年南渡的道士中,最有名的是干吉(一作于吉)和左慈。干吉是琅琊人,“先寓居东方,往来吴会,立精舍,烧香读道书,制作符水以治病,吴会人多事之”。他是《太平经》的传承者。(49)左慈是庐江人,据称汉末渡江至江南,不少名山留下了他的传说和遗迹。他似乎是江南丹法的传入者,葛洪曾说:“江东先无此书,书出于左元放,元放以授余从祖,从祖以授郑君,郑君以授余,故他道士了无知者也。”(50)江东地区“先无”的“此书”,指左慈所传《太清丹经》、《九鼎丹经》、《金丹液经》等。
永嘉之乱以后,南渡流民中有不少道士。葛洪说:“往者上国丧乱,莫不奔播四出。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,阅见流移俗道士数百人矣。或有素闻其名,乃在云日之表者。”(51)这些“流移”于江南的道士们,是神仙知识的重要宣传者。葛洪讥刺说:
余昔数见杂散道士辈,走贵人之门,专令从者作为空名,云其已四五百岁矣。人适问之年纪,佯不闻也,含笑俯仰,云八九十。须臾自言,我曾在华阴山断谷五十年,复于嵩山少室四十年,复在泰山六十年,复与某人在箕山五十年,为同人遍说所历,正尔,欲令人计合之,已数百岁人也。于是彼好之家,莫不烟起雾合,辐辏其门矣。(52)葛洪所云,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大量道士涌入江南地区后,为吸纳信众进行的“欺诳”行为。从他的批评可以推想,应该有不少江南旧民被吸纳为信众。《太平御览》卷716《服用部一八》引《名山略记》称:“郁州道祭酒徐诞常以治席为事,有吴人姓夏侯来师诞,忽暴病死。”郁洲旧属东海郡,可知有吴人以北人祭酒为师。东晋初期存在于晋陵、句容的几个仙道传承线索,如魏华存、刘璞—杨羲—许谧父子,鲍靓—葛洪、许迈,紫阳真人周君、清灵真人裴君—华侨,也都可以置于这一背景下理解。(53)
渡江来到江南的“神仙侨民”,与江南旧民的关系如何呢?《真诰》卷17《握真辅第一》记有紫阳真人周君神降时与许谧的一次谈话,很值得玩味。许谧问:“昔闻先生有守一法,愿乞以见授。”紫阳真人委婉拒绝,并解释说:“昔所不以道相受者,直以吴伧之交而有限隔耳。君乃真人也,且已大有所禀,将用守一,何为耶?”陶弘景注称:“周是汝阴人,汉太尉勃七世孙,故云伧人也。”紫阳真人和原籍右扶风的清灵真人,是晋陵人华侨降神时的主角,“先后教授侨经书,书皆与五千文相参,多说道家诫行养性事,亦有谶纬”。(54)紫阳真人不肯授许谧守一法,一个重要原因是“直以吴伧之交而有限隔耳”,由此来看,侨人、吴人之间的道法传授,最初似乎仍是有所保留的。
三茅君的态度则和紫阳真人有所不同。《真诰》卷2《运象篇第二》:
东卿司命甚知许长史之慈肃。小有天王昨问:“此人今何在?修何道?”东卿答曰:“是我乡里士也。内明真正,外混世业,乃良才也。今修上真道也。”大茅君称许谧是“乡里士”,流露出对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。陶弘景注意到此点,特别注解说:“乡里者,谓句容与茅山同境耳,非言本咸阳人也。”这一点令人很感兴趣。实际上,《真诰》神仙世界的主角就是侨居于茅山的三茅君,许谧的修道之路主要由其指引,陶弘景指出:“南真自是训授之师,紫微则下教之匠,并不关俦结之例。……其余男真,或陪从所引,或职司所任。至如二君,最为领据之主。今人读此辞事,若不悟斯理者,永不领其旨。”(55)这个观察是非常敏锐的。而三茅君对许谧的指引,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句容地方的乡土认同。这种态度与紫阳真人相比,已是很大的不同。
三茅君与白鹤庙祭祀的结合,也可以看做是其走向江南土著化的一个表现。《真诰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“汉明帝永平二年”条陶弘景注:
按三君初得道,乘白鹄在山头,时诸村邑人互见,兼祈祷灵验,因共立庙于山东,号曰白鹄庙。每飨祀之时,或闻言语,或见白鹄在帐中,或闻伎乐声,于是竞各供侍。此庙今犹在山东平阿村中,有女子姓尹为祝。逮山西诸村,各各造庙。大茅西为吴墟庙,中茅后山上为述墟庙,并岁事鼓舞,同乎血祀。盖已为西明所司,非复真仙僚属矣。据陶弘景记述,白鹤庙祭祀在茅山周边村聚极为盛行。其主庙位于茅山之东的村中,庙中有巫祝,各村又有分庙。从形式上看,显然是一种民间神祇信仰。陶弘景也意识到白鹤庙祭祀的非道教色彩,认为“盖已为西明所司,非复真仙僚属矣”。不过,白鹤庙主可能本来就非“真仙僚属”,而是常见的山神祭祀。(56)
鹤在早期的茅君传中已经出现,茅君仙去后,民众立庙供奉,“茅君在帐中,与人言语,其出入,或发人马,或化为白鹤”。可能正是这个“化为白鹤”的情节,为新茅君传记的建构提供了灵感。《茅山志》卷5《茅君真胄》:“昔人有至心好道入庙请命者,或闻二君在帐中与人言语,或见白鹄在帐中。白鹄者,是服九转还丹使,能分形之变化也,亦可化作数十白鹄,或可乘之以飞行,而本形故在所止也。”(57)九转还丹,指大茅君赐二弟“九转还丹一剂,神方一首,仙道成矣”。新茅君传记之后本来还附有这首“神方”。(58)大茅君之所以要赐二弟九转还丹,是由于二弟“已老”,“上清升霄大术,非老夫所学”。(59)在教习二弟停年不死之法并三年精思后,再赐以神丹,终成仙道。这个情节似有所指,兴宁三年的许谧,已是“年出六十,耳目欲衰”的老人。(60)
新茅君传记记述了大量茅山地理细节,《真诰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有关茅山地理环境的细致描述,即多抄自新茅君传记。这些关于茅山的“地方性知识”,内容琐碎具体,显示出撰述者对茅山地理和人文掌故的熟悉。推想起来,撰述者可能是利用了当地的白鹤信仰传说,(61)将之与仙传糅合,转化为白鹤为九转还丹使及三茅君乘鹤的情节。(62)通过这种述说方式,“神仙侨民”三茅君实现了土著化,成为江南新乡土的佑护之神,父老歌云:“茅山连金陵,江湖据下流。三神乘白鹄,各治一山头。召雨灌旱稻,陆田亦复柔。妻子成保室,使我百无忧。”(63)需要指出的是,这只是道教立场上的叙事。民间神祇被移居于此地的神仙、高僧取代或降服,在道教、佛教的“辅教故事”中是很常见的。这种叙事往往只是停留在口承或文本层面,现实中的民间祭祀仍旧延续。(64)白鹤庙在新茅君传记、《真诰》中又被称作句曲真人庙,应当理解为在不同叙事中的差异。(65)
从性质上说,三茅君是在文本上建构出来的虚拟“生命”,如何建构包括籍贯、学道经历、仙职等在内的“生命史”,反映出撰作者的理念。新传记展示的图景是:原籍关中的三茅君兄弟,渡江定居于句容茅山,成为“神仙侨民”。后来大茅君得补更高仙任,留下两位弟弟主宰茅山。他们主管、指引着江南地区侨旧民众的修仙之路和生死问题,同时也以地方神的形象佑护着茅山周边民众。很显然,“关中—茅山”是撰作者构建三茅君“生命史”的地理骨架,而“神仙侨民”对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,则是撰作者的潜在理念。在这种背景下来看杨羲对关中、茅山地理的兴趣,(66)显得饶有兴味。杨羲可能是吴人,⑨他的上清道法则传承自南渡侨民魏华存及其子刘璞。这种道法传授上的侨旧关系,应当是三茅君以及《真诰》中登场的大多数神仙均来自于北方的知识背景。(68)
三、茅山道馆的兴起及其信仰图景
东晋兴宁年间出现的新茅君传记,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茅山圣地。不过,据《真经始末》所云,杨、许降神时书写的上清文献,自太元元年许谧去世一直到义熙初年,约30年间,仅在句容、剡县等地小范围流传,读者不多。(69)这就提出一个问题:真人之诰和传记中对三茅君和茅山圣地的“塑造”,影响力究竟如何呢?
《真诰》卷13《稽神枢第三》“许长史今所营屋宅”条陶弘景注云:
长史宅自湮毁之后,无人的知处。至宋初,长沙景王檀太妃供养道士姓陈,为立道士廨于雷平西北,即是今北廨也。后又有句容山其王文清,后为此廨主,见《传记》,知许昔于此立宅。因博访耆宿。至大明七年,有术虚老公徐偶,云其先祖伏事许长史……于时草莱芜没,王即芟除寻觅,果得砖井,[上](土)已欲满,仍掘治,更加甓累。今有好水,水色小白,或是所云似凤门外水味也。王文清是句容人,他所读的“传记”,就是杨、许降神时出现的新茅君传。上引最后一句“似风门外水味”云云,亦见于《真诰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据定录君诰示,正是“传记”中的内容。王文清读“传记”并寻访许长史旧宅,是在刘宋大明年间。(70)从他的寻访活动可以获知,新茅君传记所构建的茅山圣地图景,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影响力是很有限的。(71)随着许谧父子先后去世,他们的雷平山馆久已荒废,不为人所知。王文清在刘宋中期进行的寻访活动,带有“再发现”的意味。分析起来,这种“再发现”有几个潜在的条件:其一,刘宋初期雷平山建造由长沙景王檀太妃供养的道馆,馆中的山居道士成为茅山信仰资源的寻访者;其二,新茅君传记和真人之诰在茅山道士间流传,成为寻访时的文本指南;其三,茅山周边父老的口承记忆。这些在王文清的寻访经历中都可以看到。
茅山信仰资源的“再发现”,出现于刘宋以后,似非偶然。学者已经指出,山中道馆的兴起,正是刘宋以后道教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。(72)具体到茅山而言,义熙年间(405—418)开始,杨、许手书的上清经逐渐传开,特别是经由王灵期的“造制”,影响日渐广泛,“举世崇奉”。到了梁初,已是“京师及江东数郡,略无人不有”。(73)可以想见,随着义熙以后上清经的传布,以三茅君和杨、许活动为中心的茅山信仰资源,也必然会日渐受人关注。值得一提的是,刘宋时期裴骃撰著《史记集解》时,即曾引用《太原(元)真人茅盈内纪》,(74)表明其时知识界对于新茅君传已不陌生。
茅山道馆开始增多,亦始于刘宋时期。前面提到,刘宋初期长沙景王檀太妃为其供养的陈姓道士在雷平山西北建立“道士廨”,大明年间王文清曾继任廨主。此廨及“左右空地”后来由梁武帝敕买,为陶弘景建朱阳馆。(75)山南大洞口附近,有刘宋初期广州刺史陆徽供养的徐姓女道士,弟子相承居此。刘宋元徽年间,“有数男人复来其前而居”,南齐初年王文清奉敕在此立馆,“号为崇元,开置堂宇厢廊,殊为方副。常有七八道士,皆资俸力。自二十许年,远近男女互来依约,周流数里,廨舍十余坊”。(76)另据《道学传》记载,萧道成“革命”之际,“访求道逸”,于茅山造馆,建元二年(480)敕请义兴人蒋负刍于宗阳馆行道,又敕晋陵人薛彪之为茅山金陵馆主;永明十年(492)陶弘景在中茅岭创建华阳馆;建武三年(496),薛彪之启敕于大茅山东岭立洞天馆;(77)天监三年梁武帝为许灵真敕立嗣真馆。(78)这些道馆多由皇室敕建或大族供养,与建康权力中心联系密切。(79)
据上述材料判断,茅山道馆兴起于刘宋,走向全盛则是在齐梁之际。这一点在前文所引的许长史碑、三茅君碑题名中也得到印证。其中,许长史碑阴罗列了“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”即曾支持过上清派活动的皇帝、朝臣名单,南齐有十三人,梁代有七人,包括三位皇帝(齐世祖武皇帝、太宗明皇帝、梁武皇帝)及萧遥光、萧伟、沈约、吕僧珍等朝臣。三茅君碑阴有曲阿陈师度、刘僧明分任馆主的兴齐馆、齐乡馆,兰陵鞠遂任馆主的帝乡馆,从馆名来看,这几所道馆可能与齐梁皇室有关。
这些敕建或大族供养的道馆并非纯粹支持个人修道。《道学传》“蒋负刍”条说:“负刍又于许长史旧宅立陪真馆,应接劬劳,乃以馆事付第二息弘素,专修上法也。”(80)周子良于天监十四年“从移朱阳,师后别居东山,便专住西馆,掌理外任,迎接道俗,莫不爱敬”。(81)这些需要接见道俗的“劬劳”馆务,都包括哪些内容呢?其一是斋事。天监十四年八月九日,王法明在中堂“为皇家涂炭斋”,周子良亦参加;(82)同年五月十八日,周子良与其舅徐普明在中堂“为谢家大斋,三日竟散斋”。(83)这些斋事主要为皇室、大族所做,很费精力,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》引“抱朴子曰”:“洪意谓大斋日数多者,或是贵人,或是道士,体素羸劣,不堪旦夕六时礼拜。愚欲昼三时烧香礼拜,夜可阙也。”(84)此外,梁武帝即位后曾命陶弘景炼丹,弘景并不情愿,却又不得不奉旨在积金岭东建立炼丹之所。(85)天监十四年天旱,“国主忧民乃至”,“诸道士恒章奏”,陶弘景也曾与周子良一起上章祈雨。(86)除了这些宗教活动,有时还要应对世俗杂务。句容发现的天监十五年石井栏铭文云:“皇帝愍商旅之渴乏,乃诏茅山道士□永若作井及亭十五口。”(87)句容茅山邻近建康通往三吴的交通要道破冈渎,行旅众多,茅山道士奉皇帝诏令朝廷建作井亭,正是宗教活动以外的俗务。
与茅山中道馆和宗教人口的增多有关,朝廷还专门在茅山中设立了负责治安的“逻”,《梁书》卷1《武帝纪上》记天监元年三月:
延陵县华阳逻主戴车牒称云:“十二月乙酉,甘露降茅山,弥漫数里。正月己酉,逻将潘道盖于山石穴中得毛龟一。二月辛酉,逻将徐灵符又于山东见白麞一。丙寅平旦,山上云雾四合,须臾有玄黄之色,状如龙形,长十余丈,乍隐乍显,久乃从西北升天。”天监元年三月萧衍尚未称帝,可知华阳逻南齐时已经设立。凑巧的是,逻将潘道盖也出现于天监十七年陶弘景所撰井栏记,称其为“湖孰潘逻”。(88)华阳逻可能设在陶弘景居住过的华阳馆附近,《真诰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记积金峰宜建静舍,陶弘景注云:“今正对逻前小近下复有一穴,涌泉特奇。大水干旱,未尝增减,色小白而甘美柔弱,灌注无穷。”这个逻应当就是华阳逻。此外,三茅君碑题名中有一位“宗元逻主吴郡陆僧回”。宗元逻可能与杨超远曾任馆主的宗元馆有关,(89)具体位置则不详。逻主要负责治安。为何要在茅山中设立逻呢?想来有两方面的考虑:其一当然是保障山中道馆的安全;(90)其二也可以管理、监视山中道馆的活动。(91)茅山道馆并非纯粹的世外修道之地。
根据这些迹象推断,齐梁时代的茅山实际上具有皇家、大族修道场所的意味。山中道士受到皇室、大族的供养,为皇室、大族做斋祈福,也成为他们的“劬劳”馆务。问题是,为何皇室、大族如此重视茅山?《三洞珠囊》卷2《敕追召道士品》引《道学传》称:“齐明帝践祚,恐幽祇未协,固请隐居诣诸名岳,望秩展敬。”(92)这里说“恐幽祇未协”,礼请道士们“望秩展敬”,可以理解为山中敕建、供养性道馆兴起的原因。
不过,上引《道学传》也提到,可以“望秩展敬”的名山很多,为何茅山会成为最重要的道教“圣地”?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这需要联系到三茅君的信仰吸引力。东晋中期构建的三茅君传记中,兄弟三人分别被授予仙职,大茅君是“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”,中茅君是“地真上仙定录神君”,小茅君为“司三官保命仙君”。(93)据天皇太帝敕授玉册文,其职责分别是:(1)司命君:“总括东岳。又加司命之主,以领录图籍。”(2)定录君:“兼统地真,使保举有道。”(3)保命君:“总括岱宗,领死记生。”(94)其中,司命君地位最高,“监泰山之众真,总括吴越之万神”,(95)实际上是吴越地仙和泰山鬼府的总领;定录君“兼统地真”,保命君“总治酆岱”,(96)在茅山各有“宫室”和“府曹”,“神灵往来,相推校生死,如地上之官家”,是司命君职责的具体实施者。(97)在他们的管理下,茅山成为一处“为仙真度世及种民者”通往长生度厄之路的“治所”。(98)
明白了这一点,再联系到上引“恐幽祇未协”一句,就会对茅山道馆为何在宋齐梁三朝走向兴盛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。敕建和供养道馆的皇室、大族,与普通民众一样,最关心的无非也是生死问题,(99)而三茅君正是最直接的管理者。附着在三茅君身上的这种信仰想象力,使其一旦得到某种助力,就会显示出旺盛的信仰活力。
这让人联想到宋、齐、梁三朝统治者的出身。刘裕为彭城县绥舆里人(侨置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),萧道成、萧衍为南兰陵郡兰陵县中都里人(侨置于晋陵郡武进县东城里),(100)均位于茅山东北的邻近地区,是过江侨民的集中地。三茅君碑题名中,晋陵郡、南兰陵等也正是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。这一地区侨民的信仰状况,《冥祥记》提供了一个具体事例。故事主角是刘宋元嘉年间居于晋陵东路城村的刘龄:
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,父暴病亡。巫祝并云:家当更有三人丧亡。邻家有道士祭酒,姓魏名叵,常为章符,诳化村里。语龄曰:君家衰祸未已,由奉胡神故也。若事大道,必蒙福祐。不改意者,将来灭门。龄遂亟延祭酒,罢不奉法。……像于中夜又放光赫然。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,亦有惧畏灵验密委去者。叵等师徒犹盛意不止。被发禹步,执持刀索,云:斥佛还胡国,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。(101)这是一则佛教立场上的叙事,反映出各种信仰势力在晋陵东路城村的紧张关系。当地祭酒有20人左右,足见道教信仰之盛行。与此相关,南东海郡郯县也有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冲突:“郯县西乡有杨郎庙。县有一人,先事之,后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,遇谯郡楼无陇诣褚,共至祠舍,烧神坐器服。”(102)楼无陇是原籍谯郡的侨民。在这则记事中,“求入大道”者最终受到杨郎神的惩罚,其叙述立场明显倾向于民间神庙。而抛开两则故事的叙述立场不论,京口、晋陵侨民中道教信仰显然是极为普遍的。(103)可以想见,随着刘宋以后京口、晋陵侨民政治地位的上升,道教活动会获得相当的“助力”。这或许是茅山道馆与宋、齐、梁三朝皇室关系密切的原因。
不过,从《冥祥记》的故事来看,侨民对于“大道”的认识和理解,大概只是停留在“神不饮食”、“师不受钱”、符章解厄等层面,(104)至于上清派的存思升仙之法,很难说是否流行。不仅如此,侨民对“大道”的信仰也并不纯粹。上述两则记事就出现了巫祝、神庙、佛教等多种信仰势力。此外,侨居于晋陵南沙县的临淮射阳人王敬则,其母是女巫,敬则却“诣道士卜”,还曾在暨阳县神庙“引神为誓”,(105)信仰十分多元。事实上,尽管南朝时期天师道在经义中对民间巫道曾多有批判,(106)但落实到日常信仰层面,民众是很难将其截然分开的。永嘉乱后南渡隐居茅山的博昌人任敦曾感叹说:“众人虽云慕善,皆外好耳,未见真心可与断金者。”(107)这一感叹应当就是鉴于民众的多元信仰心态。
任敦的感叹中隐含着理解齐梁时代茅山道教世界的重要线索。从齐明帝“恐幽祇未协”,梁武帝即位后“犹自上章”、(108)命陶弘景炼丹,还有皇家涂炭斋、谢家大斋的记载来看,齐梁皇室、大族供养茅山道馆的目的,是比较实际的。这也让人想起陶弘景对南洞口附近道士们的批评,即所谓“学上道者甚寡,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而已”。
陶弘景批评中,最值得玩味是“不过”一词。他显然是认为,修道者有两个层次,较低的层次是“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”,较高的则是“上道”。但“上道”与“灵宝斋及章符”并非对立关系,修“上道”者同时也会“修灵宝斋及章符”。如南岳夫人魏华存“为女官祭酒,故犹以章符示迹”。(109)陶弘景道团同样如此,王法明曾为皇家涂炭斋,周子良和徐普明曾为谢家做大斋。周子良姨母“常修服诸符,恒令为书”;又曾命周子良、潘渊文曾共作条疏辞牒为陶弘景上章。(110)另外前面提到,天监十四年干旱,“诸道士恒章奏,永无云气”,陶弘景和周子良亦共作章奏祈雨。陶弘景所编《登真隐诀》中也有关于章符的专门记述。(111)由此来看,斋法、章符是齐梁时代茅山道馆共有的道法活动。
明确了这一点,就可以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:为何三茅君碑和许长史碑题名有明显差异?许长史碑全部是上清弟子,三茅君碑则包括天师后裔、三洞法师、上清道士等多种身份。这种差异显示出以陶弘景为核心的上清道团与茅山道教的关系。齐梁时代的茅山“诸馆”,可能有一些共有的道法活动,陶弘景提到的“灵宝斋及章符”,可以理解为是对这些道法活动的一个概括。上清道团的修道方式则超越于此,更注重存思诵读的上清“大道”,成为与其他道士的区别。(112)以往的道教史研究特别注重上清、灵宝、天师等道派分野,成果令人瞩目,但对于道教的日常图景而言,“异”虽然重要,“同”也是不能忽视的。(113)毕竟,日常性的民众信仰实践,主要还是斋法、章符等道法活动。
三茅君碑立碑地点的疑问也自然而解。南洞口虽然被陶弘景批评为“秽炁”之地,但大茅山本是大茅君的洞府所在,尤其以山顶和山南洞口最为“神圣”。其中,山顶“每吉日,远近道士咸登上,烧香礼拜”,许谧亦曾“操身诣大茅之端,乞特见采录,使目接温颜,耳聆玉音”。而山南大洞口“大开”,更便于寻访参拜。山南还有被称作南便门的小洞口,“亦以石填穴口,但精斋向心于司命。又常以二日登山,延迎请祝,自然得见吾也”。在这几处适合立碑的大茅山“圣地”之中,山顶登临不便,“无复草木,累石为小坛。昔经有小瓦屋,为风所倒”,南便门“小穴甚多,难卒分别”,均远不如洞口大开,“有好流水而多石,小出下便平”且道馆密集的大洞口附近合适。(114)
从性质上来说,南朝时代的茅山,是“为仙真度世及种民者”共同的圣地,并不仅仅是上清道士的舞台。其中,“为仙真度世”者包含了多种修道团体,“种民”则是向善民众,(115)二者亦即每年三月十八日登山集会的“道俗”。三茅君虽然是上清系道士构建出来的神仙,其在齐梁时代的信仰活力,却是与一般“道俗”的信仰实践密不可分的。天监四年陶弘景祈雨上章时提到,希望三茅君显灵降雨,如此则“白鹄之咏,复兴于今”。这种心态正是理解三茅君信仰的关键。概括言之,三茅君之所以能得到茅山周边“道俗”的隆重崇拜,一方面得益于其佑护新乡土的“土著化的神仙侨民”身份;另一方面,他们主管着学道者的升仙之路和民众生死问题,这正是南朝“道俗”最关心的问题。
由此也让人对立碑时间产生一些推测。如所周知,梁武帝即位初年仍崇重道法,天监四年以后则日渐倾向于佛教,并“博采经教,撰立戒品”,于天监十八年四月八日“发弘誓心,受菩萨戒”,大赦天下,成为“皇帝菩萨”。(116)在佛教日益隆盛的格局之下,道教的前景不容乐观。隋费长房撰《历代三宝纪》卷3称天监十六年六月“废省诸州道士馆”,(117)虽然此事的真实性尚无法确认,但佛长道消的趋势是很明显的。普通三年即梁武帝受戒三年之后,道士正主持在“圣地”茅山建立三茅君碑,详细刻写天皇太帝授三茅君的九锡玉册文、三茅君小传和茅君事迹,碑阴题刻90余位“齐梁诸馆高道”和信众,差不多同时又在许长史碑阴补刻“王侯朝士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”名单,这种浓重的信仰总结和纪念意味,或许可以理解为道教徒在佛教隆盛的“压迫”形势下作出的应对之举。(118)张绎所撰碑文中的“念至德之日道,惧传芳之消歇”云云,可能是有意有所指的。
结 语
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,对江南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。由皇室、士族、庶民、军士以及僧人、道士、巫祝等各色人等构成的庞大人群,短时期内集中涌入江南地区。他们带来的文化观念、生计习惯以及信仰传统,也随之进入江南地区,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相关区域的社会历史面貌。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流民最为密集的建康以东沿江和京口、晋陵地区。可以说,“徐兖化”是东晋以后这一地区的重要特征。
《真诰》中的“神仙侨民”叙事,就是这种移民社会的反映。《真诰》神仙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,是承认“神仙侨民”在江南神仙世界中的优势地位,(119)并力图塑造其对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。其中,影响最大的是原籍咸阳、侨居茅山的三茅君。他们被赋予的职责是“监泰山之众真,总括吴越之万神”,总管着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。这种“宗教想象力”,与侨民在东晋政治中的优势地位是一致的,与此同时,也隐含着江南寒门、寒人对于一个更加“开放”的体制的渴望。(120)
“宗教想象力”的背后,是正在走向土著化的江南侨民。永嘉乱后进入江南的流民群体,在经历最初的优待政策后,自东晋中后期开始不断面临着被“土断”为江南人的命运。(121)虽然侨人士族仍标榜自己的北方郡望,但侨民们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江南人,与江南新乡土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。土著化了的江南侨民们,显然更愿意接受一个经历相似的神祇,融合侨、旧两种色彩的神仙三茅君由此获得了成长空间。三茅君对于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,也使其很容易为旧民所接受。这是在侨旧融合的政治体制下,侨旧民众相互作用而带来的一种协调。句容茅山的圣地化过程,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信仰图景。如同现实世界一样,神仙世界的侨旧融合也并不是单线的侨民化,而是在上层表现为侨民化,下层仍保持着土著信仰的底色。南朝江南的社会文化,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复合面貌。
最后想要指出的是,茅山本身也让人看到一些“侨置”的影子。大茅君的位号是“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”,保命君则“总括岱宗,领死记生”,信仰职责均与东岳泰山有关。这种观念有其来历。如所周知,汉晋民众的生死问题本来是由泰山府君掌管的,永嘉之乱后,泰山大部分时间处于胡人政权的统治之下,侨居江南的流民死后归往何处,成为一个显见的问题。在这种背景下,三茅君以仙人身份被任命“断制”泰山生死,并将管理机构分别设置于句容茅山和会稽东南滨海的霍山,④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解决了上述信仰难题。“神仙侨民”依存于江南新乡土,其权力却仍然与沦为胡人统治的泰山信仰有关,这是江南侨、旧关系的反映,也是“圣地”茅山的信仰意义所在。在梁武帝中期佛教日益隆盛的形势下,道教徒在“圣地”茅山建造总结三茅君信仰的纪念石刻,并在许长史碑阴补刻“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”名单,具有一定的宗教抗争意味。
注释:
①相关学术史梳理,参见胡阿祥:《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》,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8年,第12—33页;中村圭爾:《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》,東京:汲古書院,2006年,第3—66頁。
②这个问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触及,在侨旧学风、语言习惯、族群关系、身份性婚姻圈、土地秩序、物质文化、宗教信仰、社会风气等方面,取得了不少深具启发意义的成果,如唐长孺:《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》,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,第338—368页;陈寅恪:《东晋南朝之吴语》,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1年,第304—309页;陈寅恪:《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》,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1年,第78—119页;周一良:《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》,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33—101页;中村圭爾:《六朝貴族制研究》,東京:風間書房,1987年,第359—398頁;唐长孺:《南朝的屯、邸、别墅及山泽占领》,《山居存稿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,第1—26页;中村圭爾:《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》,第323—383頁;Michel Strickmann, "The Mao Shan Revelations: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," T'oung Pao, vol. 63, no. 1, 1977, pp. 1-64;曹文柱:《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8年第2期;李伯重:《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5年第6期。但落实到具体的地理空间内、从细部上呈现侨旧民众生活图景的研究,仍然比较缺乏。
③关于永嘉乱后江南侨民的分布,参见谭其骧:《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》,《长水集》上册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9年,第206—229页;胡阿祥:《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》,第309—338页;葛剑雄主编:《中国移民史》第2卷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7年,第307—412页。
④关于东晋南朝道教上清派特别是陶弘景,研究成果数量繁多,张超然有颇为细致的梳理,可以参见氏著:《系谱、教法及其整合: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》,博士学位论文,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,2007年,第1—21页。此外,也可以参见索安(Seidel. Anna):《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》,吕鹏志、陈平等译,北京:中华书局,2002年,第23—26页。为避免繁琐,这里不再赘述。
⑤张君房编:《云笈七签》卷27《洞天福地》,李永晟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,2003年,第611页。
⑥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朱越利译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6年,第349页。关于茅山宗教地理的概要介绍,参见三浦国雄:《洞天福地小論》,《中国人の卜ポス》,東京:平凡社,1988年,第71—112頁;Edward H. Schafer, Mao Shan in T'ang Times, Monograph No. 1, Revised edition, Boulder, Colorado: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, 1989, pp. 1-9.
⑦王明: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卷4《金丹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85页。葛洪提到的江南名山有晋安霍山,东阳长山、太白山,会稽四望山、大小天台山、盖竹山、括苍山。通检《抱朴子》内、外篇,均未提及句容茅山。
⑧已有学者注意到杨羲、许谧父子降神与东晋政治、社会结构的关联,如Michel Strickmann, "The Mao Shan Revelations: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," T'oung Pao, vol. 63, no. 1, 1977, pp. 1-64;都築晶子:《南人寒門·寒人の宗教的想像力につぃて》,《東洋史研究》47—2,1988年,第24—55頁。不过,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杨羲、许谧父子的籍贯和身份,对于神仙三茅君较少讨论。另外,茅山附近曾发现过东莞侨民刘岱的墓志,参见镇江市博物馆:《刘岱墓志简述》,《文物》1977年第6期。
⑨《茅山志》卷1《诰副墨》、卷20《录金石》、卷15《采真游》,《道藏》第5册,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出版社、天津古籍出版社,1988年影印本,第550—551、630—632、617—619页。另外,《曾巩集》卷50《金石录跋尾》“茅君碑”条对此碑有简单介绍(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,第680页);南宋陈思《宝刻丛编》卷15《建康府》“梁茅君碑并两侧题名”条引《集古录目》、《复斋碑录》,亦有简要著录。(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1辑第24册,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2年,第18325页)
⑩《茅山志》卷5《茅君真胄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75—581页;张君房编:《云笈七签》卷104李遵《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》,第2254—2262页。一般认为,《茅君真胄》更接近于东晋中期《茅传》的内容。关于《茅君真胄》和李遵传记的文本比较,参见李丰楙:《汉武内传研究——汉武内传的著成及其衍变》,《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》,台北:学生书局,1986年,第30一31页;Isabelle Robinet,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'histoire du , Paris, Publications de l' Ecole d' -Orient, vol. 2, 1984, p. 390. 笔者不习法文,此处参据张超然:《系谱、教法及其整合: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》,第90页。
(11)参见刘琳:《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1年第5期;刘屹:《敬天与崇道——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5年,第607页。
(12)《茅山志》卷5《茅君真胄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80页。
(13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第364页。
(14)这种集会直到唐代中期仍很兴盛。《全唐文》卷377录唐宪宗大历十三年(778)柳识《茅山白鹤庙记》称“每岁春冬,皆有数千人,洁诚洗念,来朝此山”。(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3828页)
(15)《太平御览》卷666《道部八·道士》引《道学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0年,第2973页。
(16)《隋书》卷27《百官志中》记北齐崇虚局职责是“掌五岳四渎神祀,在京及诸州道士簿帐等事”。(北京:中华书局,1973年,第755页)萧梁崇虚馆职责当与之类似。
(17)《太平御览》卷666《道部八·道士》引《道学传》:“(张绎)作茅山南洞碑,甚工。”(第2975页)
(18)《茅山志》卷20《录金石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630—632页。
(19)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1辑第24册,第18325页。
(20)周显明生于“己卯”年,即刘宋元嘉十六年(439),立碑时如果还在世,已有八十多岁。
(21)《茅山志》卷15《采真游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617—619页。其中杂有一位僧人:“菩提白塔行禅比丘会稽释智渊,业总五乘,义该两教。”按,菩提白塔为天监十五年陶弘景所建,事见清顾沅钩本《梁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》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3辑第2册,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6年,第570页。《茅山志》卷20《录金石》等所录碑文不见此事,似是有意删去,参见陶弘景著,王京州校注:《陶弘景集校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172页。
(22)华阳馆、崇元馆、金陵馆、招真馆、林屋馆,均见于《上清道类事相》卷1《仙观品》(《道藏》第24册,第874—878页);曲林馆见于陶弘景《茅山曲林馆铭》(陶弘景著,王京州校注:《陶弘景集校注》,第194页);北洞馆当位于茅山北洞,方隅馆当位于茅山北部的方隅山(燕口山),天市馆取自大茅山天市坛传说,金陵馆当与茅山金陵之地有关。(以上均见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第356、438、362、346页)此外,茅真馆、鹄鸣馆从馆名来看也当与茅山有关。不过,道馆同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,吴郡海虞县虞山也有天师第十二代孙张裕所建的招真馆,《琴川志》卷13《虞山招真治碑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第2册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,第1275—1276页。
(23)齐梁山中道馆地域分布很广泛,参见都築晶子:《六朝後半期にぉける道館の成立》附《南朝道館表》,《小田羲久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集》,京都:龍谷大学東洋史学研究会,1995年,第344—347頁。
(24)《太平御览》卷666《道部八·道士》引《道学传》,第2975页。
(25)陶弘景在茅山中换过好几处居所,扼要情况见《许长史旧馆坛碑阴》所刻小传:“永明十年壬申岁,投绂栖山,住中茅岭上,立为华阳馆。至梁天监四年,移居积金东涧。……十四年冬,徙来此馆。十五年,移郁冈斋室静斋。”(陶弘景著,王京州校注:《陶弘景集校注》,第186页)
(26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第347页。
(27)本段引文均见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第356、366页。
(28)据陶弘景记述,南齐初年敕建的崇元馆即位于此处。此外,可考者还有张元妃所造的玄明馆、张允之所造的金陵馆等,均见《上清道类事相》卷1《仙观品》引《道学传》,第877—878页。
(29)此碑有多家著录,录文比勘参见陶弘景著,王京州校注:《陶弘景集校注》,第171—190页。另可参见李静:《〈许长史旧馆坛碑〉略考》,《宗教学研究》2008年第3期。
(30)《梁书》卷37《谢举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3年,第529—530页。谢举于天监十四年出为宁远将军、豫章内史。十八年入为侍中,领步兵校尉。普通元年出为贞毅将军、太尉临川王长史。
(31)《六朝事迹编类》卷14《碑刻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141页)、《宝刻丛编》卷15《建康府》“梁华阳石碣颂”条引《复斋碑录》(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1辑第24册,第18324页),均指出了此碑碑阳、碑阴的时间差异,但没有注意到碑阴实际上也存在补刻现象。另据《茅山志》卷20《录金石》,此碑在唐大历十三年进行过一次“洗刻”(《道藏》第5册,第634页),《六朝事迹编类》称“唐紫阳观主刘行矩等重勒”,应当就是指这次“洗刻”。题名中径称“梁武皇帝”,王家葵认为就是重刻时所改,《陶弘景丛考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03年,第366—367页。
(32)麦谷邦夫:《梁天监十八年纪年有铭墓砖和天监年间的陶弘景》,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:《日本东方学》第1辑,北京:中华书局,2007年,第80—97页。关于墓砖的发现过程及其相关研究,另可参见陈世华:《陶弘景书墓砖铭文发现及考证》,《东南文化》1987年第3期。
(33)碑阴称:“此碑有如玄孱宿构,略有四事:一者,工人凿山,唯得此碑,一石有如现成;二者,众石悉不堪作趺,唯所指安碑处,一石有如伏龙之状;三者,密石连环,唯安柱处有自然埳;四者,事竟,洞内飞泉忽涌。”(《茅山志》卷20《录金石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632页)
(34)相关研究参见张超然:《系谱、教法及其整合: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》,第113—119页。
(35)葛洪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则完全未提及茅君,只提到仙人陈安世,以“入山辟虎狼符”著称。(王明: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卷17《登涉》,第310页)
(36)东汉时有陈留人茅季伟,为太学生,曾与汉末党人颇有关系,但未见有学仙事迹。(《后汉纪》卷22《孝桓皇帝纪下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2年,第419页)
(37)张超然:《系谱、教法及其整合: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》,第89—112页。张超然注意到,相对于紫阳真人跋涉山岳的修道方式,寻求名师。注重存思诵读的上清经法更便于修行,对于身在官场的许谧更有吸引力。但即便如此,许谧仍犹豫不决。杨羲为此做了不少努力,真人不断发出诰示敦促许谧,并为其构设了一位仙偶云林夫人。关于后者的具体讨论,可以参见李丰楙:《魏晋神女传说与道教神女降真传说》,《误入与谪降: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》,台北:学生书局,1996年,第163—183页。
(38)现存有两种版本的《神仙传·茅君》,差异极大。《四库》本内容较多,情节与李遵撰三茅君传记相似,《汉魏丛书》辑本与《太平广记》卷13“茅君”相同,较简略,具体比勘参见葛洪撰,胡守为校释:《神仙传校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0年,第182—189页。从顺序上说,应当是先有《汉魏丛书》辑本内容,后来有东晋中期所出李遵撰本,《四库》本最为晚出,明显是在李遵撰本基础上删改而成的。
(39)《史记》卷6《秦始皇本纪》记有齐客茅焦,颇有事迹。(北京:中华书局,1982年,第227页)
(40)《太平广记》卷13“茅君”条,北京:中华书局,1961年,第87—88页。
(41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《运象篇第一》,第7—9页。
(42)《紫阳真人内传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42页。
(43)张君房编:《云笈七签》卷105《清灵真人裴君传》,第2263页。
(44)《太平广记》卷58“魏夫人”条,第357页。颜真卿《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》文字稍有差异。(《颜鲁公集》卷9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,第57—61页)关于南岳魏夫人信仰,参见爱宕元:《南嶽魏夫人信仰の變遷》,吉川忠夫編:《六朝道教の研究》,東京:春秋社,1998年,第377—395页。魏华存、刘璞均实有其人,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墓地出土刘璞之女刘媚子墓志,提供了重要佐证,具体讨论参见周冶:《南岳夫人魏华存新考》,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06年第2期。
(45)《晋书》卷95《艺术·鲍靓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2482页;张君房编:《云笈七签》卷106《鲍靓真人传》。(第2318页)二者所记籍贯不同。
(46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4《稽神枢第四》,第448页。
(47)赵益对上清系“传说人物”籍贯有过统计,参见氏著: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论考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93—95页。此外,王青也注意到上清系神仙的北方特征。(《〈汉武帝内传〉与道教传经神话》,收入《先唐神话、宗教与文学考论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7年,第269—272页)
(48)《太平广记》卷7“王远”条,第45—48页。本条原出《神仙传》,《汉魏丛书》本《神仙传》与之相同,《四库》本则颇有文字差异,具体比勘参见葛洪撰,胡守为校释:《神仙传校释》卷3“王远”,第92—118页。
(49)《三国志》卷46《吴书·孙策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2年,第1110页。
(50)王明: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卷4《金丹》,第71页。参见吉川忠夫:《師受考》,《六朝精神史研究》,京都:同朋舎,1984年,第425—461頁。
(51)王明: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卷4《金丹》,第70页。
(52)王明: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卷20《祛惑》,第346页。
(53)镇江丹徒县焦湾侯家店曾出土过一枚道教六面铜印,刻有“东治三师”、“□□王氏”、“民侨”等文字,参见刘昭瑞:《镇江出土东晋道教印考释》,《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7年,第158—167页。曾维加推测其中的“王氏”可能是琅琊王氏,《“永嘉南渡”与天师道的南传——再论焦湾侯家店道教六面铜印》,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1年第3期。魏华存在世时亦为女官祭酒,“领职理民”,《太平广记》卷58“魏夫人”,第358页。需要指出的是,南渡侨民带来的信仰不仅是道教,佛教亦然,参见吉川忠夫:《五、六世紀東方沿海地域と仏教——摄山棲霞寺の歷史にょせて》,《東洋史研究》42—3,1983年,第1—27页。
(54)《紫阳真人内传》附《周裴二真叙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48页。关于《紫阳真人内传》的文本分析,可参见张超然:《系谱、教法及其整合: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》,第23—46页。
(55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9《翼真检第一》,第566—567页。
(56)如临海白鹄山山神就与白鹤有关,《太平御览》卷582《乐部二十·鼓》引《临海记》,第2625页。关于原始三茅君信仰的山神属性,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,参见Edward H. Schafer, Mao Shan in T'ang Times, p. 4;赵益:《句曲洞天:公元四世纪上清道教的度灾之府》,《宗教学研究》2007年第3期。茅山的白鹤是三只,当与茅山三峰突出的地理特征有关。
(57)本条亦简略见于《初学记》卷30《鸟部·鹤》引李遵《太元真人茅君传》(北京:中华书局,2004年,第727页),可证《茅君真胄》确实更接近东晋中期的茅君传记。
(58)《太平御览》卷678《道部二十·传授上》引《登真隐诀》:“李翼,字仲甫,以七变法传左慈,慈修之,以变化万端。此经在《茅真人传》后,道士以还丹方殊密,故略出,别为一卷。”(第3025页)可知“神方”本附于新茅君传记之后,后来才成为单行本。
(59)《茅山志》卷5《茅君真胄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78页;张君房编:《云笈七签》卷104《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》文字表述稍异(第2259页)
(60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《运象篇第一》、卷9《协昌期第一》,第19、281—282页。
(61)吴越地区白鹤信仰早有传统,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第四》说,吴王女滕玉死,发丧时“乃舞白鹤于吴市中”。(周生春:《吴越春秋辑校汇考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53页)
(62)神仙乘鹤的例子,亦见于刘向《列仙传》卷上“王子乔”条,其升仙之时,“乘白鹤驻山头,望之不得到,举手谢时人,数日而去,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”。(《道藏》第5册,第68页)薛爱华(Edward H. Schafer)对茅山白鹤意象及其文学表现有过分析。(Edward H. Schafer, "The Cranes of Mao-shan," in M. Stricmann, ed.,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. A. Stein, vol. 2, MCB XXI, Bruxelles, 1983, pp. 372-393)
(63)《茅山志》卷5《茅君真胄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80页;本条亦见于《初学记》卷30《鸟部·鹤》引李遵《太元真人茅君内传》(第727页),文字小异。
(64)参见魏斌:《宫亭庙传说: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》,《历史研究》2010年第2期。
(65)据新茅君传所记,汉代朝廷曾三次封赐或修庙,分别是王莽地皇三年(公元22年)七月,“遣使者章邕赍黄金百镒、铜钟五枚,赠之于句曲三仙君”;东汉建武七年(公元31年)三月,“遣使者吴伦赍金五十斤,献之于三君”;东汉永平二年(公元59年)敕郡县修庙。(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第360—361页)这些记事完全不见于东汉文献,薛爱华认为是撰述者虚构,参见Edward H. Schafer, Mao Shan in T'ang Times, p. 4. 其意图可能是借朝廷权威“宣示”三茅君早在汉代已定居茅山。
(66)前面提到杨羲曾抄写《关中记》。此外,他对茅山的地理环境也做过实地考察,其与许谧书信称:“不审尊马可得送以来否?此间草易于都下。彼幸不用,方欲周旋三秀。数日事也。”所谓“三秀”,即指茅山三蜂,陶弘景注云:“凡云三秀者,皆谓三茅山之峰,山顶为秀,故呼三秀也。”(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7《握真辅第一》、卷2《运象篇第二》,第535、67页)
(67)杨羲的籍贯尚不确定,《真诰》卷20《真胄世谱》称其“本似是吴人,来居句容”,“本似是”云云,说明陶弘景对此是抱有疑问的。(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,第592页)此外,有关杨羲的几种晚出传记,在提及籍贯时亦颇为模糊,如张君房编:《云笈七签》卷106《杨羲真人传》称“不知何许人也”(第2317页);《侍帝晨东华上佐司命杨君传记》则未提及籍贯(《道藏》第34册,第475—480页);《三洞群仙录》卷2“杨君司命”条引《真诰》,记为“句容人”(《道藏》第32册,第243页);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24《杨羲》称“似是吴人”,与《真诰》相同。(《道藏》第5册,第238页)
(68)三茅君籍贯是咸阳南关,值得注意的是,《真诰》中有不少神仙来自关中,如杜契、陈世京、乐长治、孟先生等,鲍靓先世似乎是京兆杜陵人。(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,第421、424、380页)许迈提到的茅山仙人陈安世也是京兆人。(《太平广记》卷5“陈安世”条,第37页)
(69)《真诰校注》卷19《翼真检第一》,第572—574页。许谧去世后,由其孙许黄民收集保存,“亦有数卷散出在诸亲通间”,在句容有小范围流传。元兴三年许黄民携赴剡县,居于马朗家,“于时诸人并未知寻阅经法,止禀奉而已”。义熙年间晋安郡吏王兴写有两通,一由孔默携回建康,后“焚荡,无复孑遗”。一由王兴自携,后“遇风沦漂”,仅余《黄庭》一篇。可知杨、许降神后的几十年间,这批资料的流传是很有限的。参见陈国符:《道藏源流考》上册,北京:中华书局,1963年,第19—28页。
(70)王文清对杨、许所书上清经很有兴趣,曾从句容葛永真处得到杨羲书《王君传》,还在大明七年饥荒少粮时,以“钱食”从句容严虬处求得许翙书《飞步经》。(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20《翼真检第二》,第581页)这两种资料应当就是“数卷散出在诸亲通间,今句容所得者是也”。
(71)杨、许降神在当时并非秘密。《真诰》卷17《握真辅第一》“今具道梦”条陶弘景注称:“于时诸贵游或闻杨降神,信者多所请问,不信者则兴诮毁,故有此言以厉之。”(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,第540页)其时许谧尚在官场任职,降神的一些内容可能因此有所流传。
(72)参见都築晶子:《六朝後半期にぉける道館の成立》,第317—352其。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,小林正美推测或许与刘裕对孙恩、卢循之乱的镇压有关。(小林正美:《六朝道教史研究》,李庆译,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1年,第198页)关于刘宋时期江南道教的变化,另可参见唐长孺:《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》,《山居存稿续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,第182—201页。
(73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9《翼真检第一》,第572—575页。早期灵宝经也受到上清经的影响,参见Stephen R. Bokenkamp, "Sources of the Ling-pao Scriptures," in M. Strickmann, ed.,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. A. Stein, vol. 2, MCB XXI, Bruxelles, 1983, pp. 434-486; 王承文:《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2年,第210—220页。刘宋以后灵宝经的广泛流行,可能也会促进上清系神仙知识的传播。
(74)《史记》卷6《秦始皇本纪》裴骃集解引《太原真人茅盈内纪》,第251页。裴骃为裴松之之子,《史记集解》撰述的具体时间不详。
(75)《周氏冥通记》卷3“七月十八日夜”条陶弘景注,参见麦谷邦夫、吉川忠夫編:《周氏冥通記研究(訳注篇)》,京都: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,2003年,第183—184頁。
(76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第366页。
(77)蒋负刍、薛彪之事,均见《上清道类事相》卷1《仙观品》引《道学传》,《道藏》第24册,第877页。
(78)《茅山志》卷15《采真游》、卷20《录金石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617、633页。
(79)陶弘景与建康权力中心的联系自不必言,再如茅山女道士晋陵人钱妙真去世后,门人立碑,“邵陵王为观序,今具存焉”。(《太乎御览》卷666《道部八?道士》引《道学传》,第2973页)另外,关于早期茅山道馆,都築晶子亦有梳理。(《六朝後半期にぉける道館の成立》,第321—333頁)
(80)《上清道类事相》卷1《仙观品》引《道学传》,《道藏》第24册,第877页。
(81)《周氏冥通記研究(訳注篇)》卷1“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”条,第9頁。
(82)参见《周氏冥通記研究(訳注篇)》卷3“八月九日”条,第199頁。涂炭斋的起源,目前存在争议,王承文认为是早期天师道已有的斋法。(《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》,第343—354页,吕鹏志则认为出现较晚,是模似灵宝斋制立的《唐前道教仪式史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8年,第220—225页)
(83)《周氏冥通記研究(訳注篇)》卷1“周所住屋南步廊”条,第25頁。
(84)《道藏》第9册,第874页。《三洞珠囊》卷5《长斋品》引录此条,文字小异,《道藏》第25册,第324页。今本《抱朴子内篇》无此内容。本条资料的使用承蒙审稿人指正,谨致谢意。
(85)《华阳陶隐居内传》卷中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05页。
(86)《周氏冥通記研究(訳注篇)》卷2“六月二十一日”条,第126—127页。
(87)《光绪续纂句容县志》卷17上《金石中》“梁石井栏题字”条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398页。
(88)《茅山志》卷8《稽古篇·陶真人丹井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90页。
(89)《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》,陶弘景著,王京州校注:《陶弘景集校注》,第186页。
(90)茅山中发生过抢劫事件,《周氏冥通记》卷3“七月十三日”条记,“十三夕一更忽被寇,似有六七人,皆执杖”(《周氏冥通記研究(訳尺注篇)》,第178頁),抢劫者自称是“御杖”。此事给周子良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,“比者恒忧与盗事”(第186页)。
(91)天监七年陶弘景因奉敕炼丹不成,“改服易氏”,从茅山逃往浙东。(《华阳陶隐居内传》卷中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06页)可见茅山道馆受到朝廷的管理、监视。
(92)《道藏》第25册,第306页。此事不见于有关陶弘景事迹的其他记载,真实性尚有待确认。不过,齐明帝由于上台前后残杀高、武子孙,的确内心颇为不安。
(93)《茅山志》卷5《茅君真胄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78—579页。
(94)《茅山志》卷1《诰副墨》,《道藏》第5册,第551页。
(95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2《稽神枢第二》,第384页。《茅山志》卷5《茅君真胄》则记作“都统吴越之神灵,总帅江左之山元”。(《道藏》第5册,第579页)
(96)《周氏冥通記研究(訳尺注篇)》巻4“十二月二十一日”条,第219页。
(97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、卷12《稽神枢第二》,第357、381—391页。
(98)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第348页。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,参见魏斌:《仙堂与长生:六朝会稽海岛的信仰意义》,荣新江主编:《唐研究》第18卷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99—125页。
(99)这一点从杨羲为自己设定的仙职,即“辅佐东华为司命之任,董司吴越神灵人鬼,一皆关摄之”,也可有所理解。(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20《翼真检第二》,第592页)杨羲的授职见《真诰》卷2《运象篇第二》,具体为“理生断死,赏罚鬼神;摄命千灵,封山召云”,“总括三霍,综御万神,对命北帝,制敕酆山”云云。(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,第54页)此条为杨羲“自记”。另外前文曾提到,从故乡东海郡渡江至江南的神仙王远,其先职也是与“地上五岳生死之事”有关。
(100)《宋书》卷1《武帝纪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1页;《南齐书》卷1《高帝纪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2年。第1页;《梁书》卷1《武帝纪上》,第1页。萧衍出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。
(101)释道世著,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: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62《占相篇》引《冥祥记》,北京;中华书局,2003年,第1865—1866页。
(102)《太平广记》卷295“侯褚”条引《异苑》,第2348页。
(103)关于徐兖地区的道教信仰传统,参见陈寅恪:《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》,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,第1—46页;刘屹:《东部与西部:早期道教史的地域考察》,《神格与地域: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1年,第173—243页。
(104)施舟人:《道教的清约》,《法国汉学》第7辑,北京:中华书局,2002年,第149—167页。
(105)《南史》卷45《王敬则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,第1127—1128页。暨阳也是过江侨民的重要居住地,《世说新语·术解》引《郭璞别传》,称其于永嘉乱后,“结亲暱十余家,南渡江,居于暨阳”。(余嘉锡:《世说新语笺疏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705页)参见《日知录》卷31“郭璞墓”条。(顾炎武著,黄汝成集释:《日知录集释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1763页)
(106)王承文:《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》,第296—319页。
(107)《三洞珠囊》卷1《救导品》引《道学传》,《道藏》第25册,第296页。
(108)《隋书》卷35《经籍志四》,第1093页。
(109)《太平御览》卷671《道部一三·服饵下》引《上元宝经》,第2991页。
(110)参见《周氏冥通記研究(訳注篇)》卷2“六月四日”、卷3“七月二日”,第82、145页。又卷1“夏至日”条称:“姨母修黄庭三一,供餋魏伝蘇伝及五岳三皇五符等。”(第43頁)
(111)《登真隐诀》卷下《章符》,王家葵:《登真隐诀辑校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,第74—79页。
(112)有趣的是,陶弘景对“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”的道士多有批评,他自己竟也成为被取笑的对象。撰作年代不详的《桓真人升仙记》(《道藏》第5册,第513—517页)称,本来做杂役的陶弘景弟子桓真人(即桓法闿)升仙,此时弘景拜托他代问自己为何一直未能升仙。此事与《周氏冥通记》中周子良升仙前“群仙来游”时的谈话情形相似。麦谷邦夫指出,天监末期的陶弘景,已经陷入非常微妙的心理状态。(《梁天监十八年纪年有铭墓砖和天监年间的陶弘景》,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:《日本东方学》第1辑,第80—97页)为何他的升仙会晚于弟子?此点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上清大道的质疑。
(113)神塚淑子注意到,刘宋以后上清派的仪礼化、教团组织化趋势,与灵宝派相似,实际上背离了最初的个人修仙理念。(参见氏著:《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》,東京:創文社,1999年,第287—291頁)
(114)本段引文均见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:《真诰校注》卷11《稽神枢第一》,第363—367页。
(115)种民概念见《太平经》卷1—17《太平经钞甲部》“种民定法本起”条。(王明编:《太平经合校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0年,第1—2页)小林正美认为,东晋南朝时期种民思想的流行,与道教终末论有关。(小林正美:《六朝道教史研究》,第435—458页)
(116)《续高僧传》卷6《义解二·释慧约传》,《大正藏》,第50册,史传部二,第469页。参见諏訪義純:《梁武帝仏教關係事蹟年譜考》,《中國南朝仏教史の研究》,東京:法蔵館,1997年,第11—78頁;颜尚文:《梁武帝受菩萨戒及舍身同泰寺与“皇帝菩萨”地位的建立》,《中国中古佛教史论》,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0年,第250—319页。
(117)《历代三宝纪》卷3“天监十六年”条,《大正藏》,第49册,史传部一,第45页。《佛祖统纪》卷37“天监十六年”条则称“敕废天下道观,道士皆返俗”,《大正藏》第49册《史传部一》,第350页。
(118)陶弘景梦佛“授其菩提记,名为胜力菩萨”(《梁书》卷51《陶弘景传》,第743页),天监十五年于茅山建菩提白塔,也可置于这一背景下理解。(参见王家葵:《陶弘景丛考》,第30—32页)
(119)小南一郎认为,上清修仙思想在南朝的流行,意味着人在神仙世界中的“卑小化”,这可能与江南豪族屈从于北方贵族的政治现实有关。(小南一郎:《尋藥から存思へ——神仙思想と道教信仰との閒——》,吉川忠夫編:《中國古道教史研究》,京都:同朋舎,1992年,第3—54頁)
(120)都築晶子:《南人寒門·寒人の宗教的想像力につぃて》,第24—55頁。
(121)关于土断的研究很多,参见胡阿祥:《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》,第89—111页;安田二郎:《僑州郡縣制と土断》,《六朝政治史研究》,京都: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,2003年,第453—524頁。南徐州的情况比较特别,新近的研究,可以参见小尾孝夫:《南朝宋斉時期の国軍体制と僑州南徐州》,《唐代史研究》第13号,2010年,第3—27頁。
(122)参见魏斌:《仙堂与长生:六朝会稽海岛的信仰意义》,荣新江主编:《唐研究》第18卷,第99—125页。